常威:论阳明心学与明代诗文理、情向度的流转丨【斯文选刊】: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论阳明心学与明代诗文理、情向度的流转
文/常威
摘要:明代诗文“载道派”与“缘情派”以阳明学为节点的分野固然是一种大势所趋,不过明代诗文的理、情向度并非呈现一种交互递嬗的局面,实际上则是一种交织、延迟又递嬗的情形泰州道观寺庙寺院。明代的诗文之辨,虽然大都将主情的诗与主理的文相对立,但是如前七子所主张的“诗主情”则饱含儒道内涵。而因为王阳明心学思想本质重儒道的倾向,兼之唐宋派继承阳明时的儒道侧重,所以重情但更重道的阳明心学并没有即刻导致明代诗文理情向度的转轨。至于阳明后学因背离阳明心学的“致”而过分强调“良知”,因而有跳脱理道的拘囿而有对个人情欲的强调,而这一转变也滋生了晚明文学重情说的蜂起,但是此期学人看似对理道的背离未尝不是对真正传统儒道的回归。
关键词:阳明学 重理 主情 流转 延迟
理、情是中国古代文论经常触及的一对范畴,时至明代,不同思想影响下的群体对理、情的认知与侧重也存在差异,尤其随着阳明心学的崛起,其对明代理、情关系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最终形成了明代诗文理、情交织、延迟又递嬗的壮丽图景泰州道观寺庙寺院。大体而言,明代的理情关系流转:
一方面基本上承续了宋代的传统,大都表现出以理学家为本以文学家为归的趋向,在本体论上主张‘文以载道’、‘诗言志’……这种观念弥漫于文坛,几乎占据主导地位泰州道观寺庙寺院。另一方面,由于明中叶以后王守仁心学的流行和人们对理学专制的反动,文学观念的情感论盛极一时。[1]
但是需要指出,明代诗文“载道派”与“缘情派”以阳明学为节点的分野固然是一种大势所趋,但是具体来说,明代诗文的理、情向度并非呈现一种交互递嬗的局面,实际上则是一种彼此交织的情形,而在流转过程中,又存在着延迟的情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这种交织一方面呈现为在载道话语盛行的明中叶以前,也有前七子诗歌主情、受地域环境等影响的吴中派人士的主情之论。而在阳明学产生之后,也不乏唐宋派重理的文学主张。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阳明学产生之前学人(如七子派等)的主情之论,实际上也固含着理道的深刻内涵,而对于那些在阳明学影响下的主情论者(如李贽等),或亦未完全背离儒道的实质。对于流转过程中的延迟而言,则表现为阳明后学在承祧阳明学意指时的不同侧重导致明代诗文主情说的风靡并非发生于阳明心学产生之际,而显然是阳明后学推助的结果。
一、明代诗文辨体与前七子“诗主情”说的理道倾向
在中国文学的历史河流中,载道与缘情观此消彼长,贯穿始终泰州道观寺庙寺院。一般而言,载道观多在王朝振兴之时,而缘情观的产生则多在朝代更迭之际。就明代而论,由于阳明心学的影响,缘情说则可上溯于明中叶,而以晚明表现最为显著。当然,欲探究明代载道与缘情向度的流转,不能不首先论及明代的诗文之辨,而溯及前七子的主情之论。
(一)七子派诗文辨体与明代诗文主情说的前奏
明代的诗文之辨,大都将主情的诗与主理的文相对立,情、理俨然成为二者的代名词泰州道观寺庙寺院。但是需要指出,在儒道昌盛的时代背景下,研习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所主张的情实未脱离理道的藩篱。 因此,就明代而言,在阳明学未产生之前,不管是诗还是文,其根本指向可以说均未超出理道的界限。
稽考可知,明初立国,去宋未远,诗、文载道传统犹存,诸如台阁体者,可为明前期载道文风之代表,故他们对于诗、文之辨的区分并不明显,在某种程度上则有混同二者的趋向,例如,苏伯衡云:“尉迟楚好为文,谒空同子曰:‘敢问文有体乎?’曰:‘何体之有?《易》有似诗者,《诗》有似书者,《书》有似《礼》者,何体之有?”[2]而至李东阳,本方孝孺“文而成音,则为之诗”(《刘氏诗序》)之说,遂谓诗、文“各有体而不相乱”(《匏翁家藏集序》),可见其“诗文之别主要在声,在于诗歌有声律可资讽咏,这对诗文体类的分别可谓一语中的泰州道观寺庙寺院。但李东阳所说的声,不在平仄而在调。”[3]复至七子派,亦明乎诗、文之辨,遂有诗主情、文主理之论。李梦阳对此的论述尤为清晰:
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矣泰州道观寺庙寺院。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4]
康海于写景、道情之载体则言“予观渼陂先生之集,其叙事似司马子长而不屑屑于言语之末,其议论似孟子舆而能从容于抑扬之际,至其因怀陈致,写景道情,则出入乎风雅骚选之间,而振迅于天宝开元之右”[5],这显然表明了载道与描摹情景所使用载体的诗文差异泰州道观寺庙寺院。以上可见七子派诗文辨体注重于理、情的差别,不过从李梦阳的论述中亦可知诗歌自然可以有理,不过理并非诗歌本色,真情才是其最终依归园地,故而“在李梦阳看来,当时的文人学子之诗乃是缺乏真情的‘韵言’,‘今之文’ 也是‘考实而无人, 抽华则无文’的没有生命力的东西, 只有民间才有真诗。”[6]不惟李梦阳如此,七子派的其他成员也多有此论。例如,徐祯卿《谈艺录》更加强调了情感为诗之源:
情者,心之精也泰州道观寺庙寺院。情无定位,触感而兴,既动于中,必形于声。故喜则为笑哑,忧则为吁歔,怒则为叱咤。然引而成音,气实为佐;引音成词,文实与功。盖因情以发气,因气以成声,因声而绘词,因词而定韵,此诗之源也。[7]
可见,在徐氏看来,因嬉笑怒骂之情而自然生发的音词,成为诗歌创作的不二法门,其实也是诗所以为诗的重要特质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平心而论,在理、情侧重上言诗文之区分并不恰切,因为不管是诗还是文,言理或抒情并非二者不可逾越的鸿沟,只要有现实的需要,似乎皆可因之成文,也正因为这样,以诗为文或以文为诗的诗文创作成为一种可能,所以说诗未尝不能载道,自然不宜落于专情之域泰州道观寺庙寺院。至于七子派所主张的“诗主情”,其实与古人所谓“诗言志”者一样,依然包含着儒家伦理道德的成分,而并未与传统“诗缘情而绮靡”的论调划出疆界。因为“诗缘情而绮靡”尽管以情作为直截的表达,但是其理论价值亦不在于其与言志的对立(事实上并不对立),而在于其抉发了诗歌的美感特征。诚如王运熙、杨明所言:
汉魏以来,情、志二字常是混用的泰州道观寺庙寺院。……可见志或情,当时都是指内心的思想感情而言,无论是关于穷通出处,还是羁旅愁怨,都既可称为志,也可称为情。因此,‘诗缘情’一语,不过是说情动于中而发为诗之意,并不具有与‘诗言志’相对立的意义。……‘诗缘情而绮靡’一语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用‘缘情’代替了‘言志’,而在于它没有提出‘止乎礼义’,而强调了诗的美感特征。[8]
至于这时的情感内涵,更大程度上属于社会、国家层面的道德情感,而非属于个人真情泰州道观寺庙寺院。对于个中原因,或在于中国古代文论往往“表现出外部形态的多样化和内部形态的单一化”的特征,因此外部形态表现出来的诸如“诗言志”、《文选注》、诗文评、总集、杂记等多样性的风貌,“基本上都是被大致相似的文学观念所支配的,这种文学观念就是由‘诗言志’、‘感物吟志’、‘思无邪’、‘兴观群怨’等几条主干构成的中国传统文学理论。”[9]换言之,“古人对于像‘情’、‘志’、‘心’、‘意’、‘理’、‘性’、‘性情’、‘性灵’之类的词汇的含义,虽然在具体讨论中可能有一定的差别,但并没有确定的区分,他们对这些词语的运用似乎也无一定之规,因此,他们所言‘情’时,未必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情’。”[10]是故,对于儒家知识分子来说,在后世以儒家主流话语作为行为处事准则的背景下,他们在文学作品上倡言的情,多少带有汉代“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意味。而这种文学观“本身就是在经书文本的阐释中形成的,是经学著作的副产品。由于经学所推崇的“五经”文本中,《诗经》与文学的关系最为直接,因此汉代的文学理论从总体上看,就形成了一种以《诗经》阐释为中心,以伦理道德规范为旨归的经学化的功利主义文学观;而‘发乎情,止乎礼义’,则是这种文学观的最高追求”[11],因此,由这样的文学主张创作的文学作品必然有合于理(儒道)的趋向。诚如詹福瑞所曰:
儒家诸子承认情的存在,是以明确的社会规范,即理性的克制、引导和自我调节为目的泰州道观寺庙寺院。他们所说的诗之情,是凝聚了理性的感性。孔子规范以无邪、不淫、不伤,荀子则归之于圣人之道,归之于礼。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儒家诸子所理解的志,是不排除情感,然而已经有了高度理性规范的思想情感。[12]
台阁派自不待言,而即使以明代主情甚力的前七子论之,亦然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二)国家与社会:七子派主情说的价值归趋
显然,前七子的主情理论依然难以挣脱儒家思想意识形态的钳制,诸如前七子的执牛耳者李梦阳虽言诗歌生于情,不过他的逻辑进路则是“诗言志,志有通塞,则悲欢以之”[13]泰州道观寺庙寺院。不宁唯是,出于对诗歌价值的体认与鲜明的尊体意识,李梦阳又有“以诗观人”之论曰:
夫诗者,人之鉴者也泰州道观寺庙寺院。……是故端言者未必端心,健言者未必健气,平言者未必平调,冲言者未心冲思,隐言者未必隐情。谛情探调,研思察气,以是观心,无庾人矣。故曰诗者人之鉴也。
值得注意的是,李梦阳“以诗观人”的参照标准,明显落于儒家的言说话语中,这一点在其稍后对林公的评述中得以窥见,其论说曰:“夫林公者,道以正行,标古而趍,有其心矣泰州道观寺庙寺院。行以就政,执义靡挠,有其气矣。政以表言,嚣华是斥,有其思矣。言以摛志,弗侈弗浮,有其调矣。志以决往,遯世无悔,有其情矣。……是故其进也有亮直之忠,匡救之直,有功事之敏,而其退也,身全而心休也。”[14]以上从李梦阳评述林公“道以正行”、“执义靡挠”、“其辞端”、“其气健”、“亮直之忠,匡救之直”诸语中,不难看出其内蕴的儒家思想精义。当然,这多少带有与传统思想观念——“以文观人”相抗衡的意味,但是这一论断在肯定诗歌的价值决不逊于文的同时,却无形中使得诗歌的功用发生了向散文靠拢的转向,从而使得诗文文体之辨在这一意义上趋向于混同。就此而言,我们从康海“诗言志”的论述中也可以窥见,其曰:“夫扬休烈,道情性,古之人莫不用之,而予意则苟求其志而已。诗曰:言志。今之为诗者,果言志否耶?夷观而试省之,则思过半矣。”[15]这里康氏将诗言志重提,明显有在诗歌创作主张上纠正李梦阳等人的诗主情说的倾向,不过二者在本质上殊途而同归,因为李梦阳等人的诗主情说其实质仍然是诗言志的归趋所在。除此之外,王世贞则有“以诗观政”之论,其曰:“李子毋疑于诗,将使李子政成,而诗郁山川之灵,致采民物之丽,衍标兹方之艺文,太师采之,庶几嗣丽《七月》哉!”[16]据上可知,七子派的诗歌主情理论,其出发点与归宿难免还要回归于儒家本位而不能不有所锢限。诚如黄卓越所曰:
七子派……无论将情感放在何种位置,其理论并未超过传统文论(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等)的阐释范围,而在对情感的定性上,或还属于那种带有明显社会倾向的情感泰州道观寺庙寺院。……说到底了,这种情感定向,仍是欲在形式讨论中复得儒家诗学的世俗宗趣。[17]
当然需要指出,七子派的主情理论亦并非完全契合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类型,因为诸如李梦阳等人的作品时往往宣露着浓郁的情感色彩,超出了中正和平的界限,而这一点则在阳明后学如黄宗羲等人有关温柔敦厚的论述更为普遍地显露出来泰州道观寺庙寺院。正因如此,他们引起了唐宋派激烈的批评。在唐宋派那里,“他们(唐宋派)认为李梦阳全凭着个人好恶感情用事,摆脱不了名利的束缚,是欲根未尽的缘故。而他们则主张彻底地排除欲念,不受喜怒哀乐、嗜好淫欲的感情骚扰,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要保持心地的宁静澄明,这才是圣人之道的表现。这样的圣人之道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应表现为个人感情受到抑制,尽量显出冲淡高远的境界。”[18] 由此而言,对于声嘶力竭宣扬诗歌主情感的七子派来说,其所言的诗出乎情之“情”仍然需中于儒道,但是又与传统的“温柔敦厚”的诗教有所不同,而超出了中正和平的界限。
二、阳明学与明代诗文理、情递嬗的延宕
如上所述,阳明学产生之前不管是重理的文还是主情的诗都明显偏向于理道,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肯定人的自然情欲的王阳明心学是否有重情甚于重理(儒道)的倾向?明代的理情侧重是否在肯定自然情欲的王阳明心学那里已经得到扭转?或亦未然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一)王阳明:道德行为中的情感认同
不可否认泰州道观寺庙寺院,阳明心学在理论建构中倡言自然人情、欲望:
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泰州道观寺庙寺院。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认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着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虽云雾四塞,太虚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灭处,不可以云能蔽日,教天不要生云。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19]
这正是其与程朱理学明显不同处,亦是其高明处所在,因为阳明肯定人的自然情欲,其本意在于“激励士人之道德修持,希望人人都能追求一种极高之道德境界,具圣人之气象泰州道观寺庙寺院。此一点,在带来自信,解除权威思想之束缚与禁锢上,影响至为深远”,于此而言,其显然比程朱“灭人欲”以达到天理的强硬手腕更为人易于接受。不过也正因为此,“此一极难得之思想突破,又为思想解放开一门径。此一门径,正通向因商业发达而改变了的社会风尚。思想之解放与其时新兴的社会风尚一拍即合,回归自我,享乐、自信、自恣、放任情欲的思想行为在社会上兴起,影响到文学上来,便表现为发抒真情,追求浅俗的创作倾向。”[20]当然需要指出,“就阳明本身来说,不但并无后学之偏,与白沙亦不同。……对于阳明,我们必须记住,一方面他对洒落自得、无滞无碍的境界有真体会,另一方面他始终坚持以有为体以无为用,以敬畏求洒落”[21],是故阳明虽然肯定情欲,但是不能不谨持敬畏之心,而其之所以肯定情欲的深层内涵,恰在于激励士人修持道德,至于其触发的思想解放实非阳明之初衷。宇文所安曰:
人的情感,一旦被发动,很容易趋于极端,而这样的极端常常和丧失自我联系在一起泰州道观寺庙寺院。(也就是说,被不断的刺激之张力所影响,结果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因此,‘节’是必要的,这样‘情’可以得到一种令人满意的限制,不至流于过分。[22]
阳明显然对此深有体悟,故而阳明心学对情的终极旨归并不是任情恣意(尽管这在阳明后学身上有所体现),而是要求以儒家伦理道德对情加以约束,故其曰:“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于此心之良知而已泰州道观寺庙寺院。此诚毫厘千里之谬者,不容于不辨,吾子毋谓其论之太刻也。”[23]又曰:“夫过情,非和也;动气,非和也;有意必于其间,非和也。”[24]
显然,在阳明心学理、情关系的论述中,虽然其肯定自然情欲的合理地位,但是应该看到,其要求的情欲含有道德的内涵,而其最终归宿还是儒道在内心的蓄积存养,而所谓情者,实际上是合理之情,中道之情,而完全不能无拘无束,更不能允许放任自流,任凭一己之情恣肆流淌泰州道观寺庙寺院。在他看来,“气和情当然是要的,如孟子‘浩然之气’,如孔夫子想见南子的‘情’。但有什么样的气,什么样的情,这却要由思想来规定。气有高低、情有上下,也要由思想来确定、规范。所以‘发乎情止乎理’与‘杀生成仁舍生取义’,才是真正的情和气。”[25]究其因,阳明心学并非是对程朱理学的反动,而同样以复兴儒道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和践履动力。因此,阳明心学纵然有肯定人的自然情欲的表述,但其“存天理、去人欲”的本质追求显然不能也不会有所改变。换言之,其对自然人欲的肯定只不过是谋取天理的手段而已,也恰因如此,所以紧接王阳明而后的唐宋派,他们在诗文理论主张上仍然固守着理道的界限。作为阳明心学的追随者,王慎中、唐顺之发挥了阳明心学本质上重儒道的一面而将之体现在文学的创作上(从这一意义上说,唐宋派比阳明后学更加贴近阳明的思想),因而他们多有文道合一之论,也难怪后七子如李攀龙批评他们曰:“今之文章,如晋江、毗陵二三君子,岂不亦家传户诵?而持论太过,惮于修辞,理胜相掩。”[26]
而时至阳明后学,他们的情感思想实有对道德评价的逾越而有近利欲的体现,例如,黄绾有重利之论:“饥寒于人最难忍,至若父母妻子尤人所难忍者,一日二日已不可堪,况于久乎?由此言之,则利不可轻矣泰州道观寺庙寺院。”[27]这显然与阳明后学对阳明思想的发挥与部分背离有关。陈谷嘉曰:
历史发展到明代,理学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如果宋代理学体现了一个‘新’字,是儒学的革新,是新儒学,如果说元代理学表现出通俗化和普及化的特点,那么明代理学所体现的是一个‘变’字,不断演变则是明代理学发展的时代特征。[28]
陈氏有关元、明理学特质的归纳,颇显功力泰州道观寺庙寺院。就明代理学的演变而言,不特标示着它由程朱理学向阳明心学的转变,也暗含着阳明心学内部的蜕分。
(二)阳明后学:道德的失语与情欲的独语
至于阳明后学与阳明学术思想的差异,于本体论上来说,阳明后学渐有由宗心向宗性转变的迹象,而“从双江、念庵、狮泉到塘南、见罗,是一个逐渐脱离阳明学的发展线索泰州道观寺庙寺院。这一线索最终指向,其实是对作为良知观念之核心内涵的‘心即理’这一阳明学的根本命题产生了怀疑。从双江、念庵质疑‘现成良知’,到见罗根本视良知为为不足为最终凭藉的已发之用而回归性体,正是‘心即理’说受到动摇这一发展线索由隐而显的表现”[29]。而于功夫论上言,陆树声曰:
阳明致良知之说,病世儒为程朱之学者支离语言,故直截指出本体泰州道观寺庙寺院。而传其说者往往详于讲良知,而于致处则略坐入虚谈名理界中。如禅家以无言遣言,正欲扫除前人窠臼,而后来学人复向无言中作窠臼也。[30]
诚如其论,阳明心学虽讲良知,但于“致”尤其侧重,自然非后来重良知而略于“致”者可同日而语泰州道观寺庙寺院。易言之,“阳明之学,以致良知三字为宗旨,而以事上磨炼为入学之门。学者苟循序着实用功,庶几可入其门而进窥其堂奥。如徒事口耳讲说,而欲明阳明之学,是所谓南辕而北其辙也。”[31]
显然,至阳明后学处,阳明心学的本体论与功夫论阵地逐渐失守,阳明学已不复其原初样貌,而有背离名教义理的趋势,是以黄宗羲曰:“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道观寺庙寺院。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32]究其因,这是“王畿、王艮这些误解了阳明的‘左翼’弟子们所著学说的后果。他们错误的声称良知是人心中现成能的、自发的,无需再道德完善上花费功夫,这一信念难免使他们错把物欲认作天理,因此沉迷于享乐”[33]。是故,“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思潮,在这问题上则是以人类的自然要求、物质欲望为出发点的(当然,这仅仅是他们所认为的自然要求和物质欲望;在这方面,必须考虑到他们的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所谓‘非民情之所欲,故以为不善’。正因如此,他们才可以把‘好货’、‘多积金宝’之类的欲望肯定为善;但也正因如此,他们就必须同时肯定‘男女之欲’(即所谓‘好色’)等其他的自然要求。”[34]
这样一来,时人不仅渐消解了道为儒道的专有归属,乃至于有“道乃道理,学乃学问,有道理,便有学问泰州道观寺庙寺院。不能者待学而能,不知者待问而知。问总是学,学总是道,故谓之道学”[35]之论,而且涤荡了阳明心学的反省自新意识:“本心之明,皎如白日,无有有过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过,当时即得本心。人孰无过?改之为贵。”[36]乃至于万历年间袁黄已有为情张目之论:“古之圣人治身以治天下,唯用吾情而已。人生于情,理生于人,理原未尝远于情也。”[37]至若晚明文人“无论是在自序里还是在回忆录的本文中,我们发现的只有渴望、眷恋和欲望,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悔恨和忏悔”[38]。因此,个人情欲便理所当然地凌驾于道德情感(五伦五常)之上。对此,沟口雄三的总结可供参照:
明末,儒学成为所谓‘自己性命’之学的探究之学,探索自己的‘本来的自然到底是什么’泰州道观寺庙寺院。他们认为,即使是贱夫卑妇,其爱子爱父之心也并无例外,其自然的情爱才是孝、是慈,因此天则不可能是超越人和自然的。他们说天理一旦被意识其存在,就已不是天理,这是主张五伦五常不应该被意识为外在的规范,它存在于不加以人为控制的状态下无法抑制而发露的人的真情之内。[39]
不过需说明的是,一直以来,“说到‘肯定欲望’,也一向并不区分这种欲望是生理的、本能的欲望还是物质欲、所有欲;朱子也好,其后明末的李卓吾也好,清中叶的戴震也好,我们都一概地用‘肯定欲望’一语加以概括泰州道观寺庙寺院。但是在这里,我要对欲望作一个区分,把前者成为个体欲望,后者称为社会性欲望,以朱子的为个体欲望、李卓吾及戴震的为社会性欲望。”[40]亦需指出,在晚明学人看来,情欲显然“不再是自我实现的道德障碍,而是人的生命力量的确证,感性要求与生生之德由对立而走向了统一。这是一种价值观念的转换,正是通过如上转换,儒家传统的人本主义开始获得了新的内涵:它已不仅仅表现为尊重主体的类的本质,而且以关怀主体的生命存在为内容。也正是这种广义的人文关怀中,个体的内在价值得到进一步的确认”[41],这大概是此期情欲之所以得到鼓吹的深层次原因。
诚然,情中于理(儒道)者不失其为理(儒道),而情过于理(儒道)者则不免近于利欲泰州道观寺庙寺院。正因为如此,所以“自明以来,文人夸毗,惟怀婚姻,自诩风流,廉耻道丧,于是有《秘辛杂事》、《飞燕外传》诸作”[42]。以此来看,此期学人对情、欲的大胆告白就不难理解了。例如,对于描写情欲而有淫书、秽著之称的《金瓶梅》,袁宏道则表达了欣赏的态度,其《与董思白》曰:“《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43]黄绾《明道编》则旗帜鲜明的为利欲张目:“饥寒于人最难忍,至若父母妻子尤人所难忍者,一日二日已不可堪,况于久乎?由此言之,则利不可轻矣。”[44]显然,这种对自然情欲的肯定不仅堪称直截,毫无忸怩遮掩之态,自然超出了儒家伦理的界限,从中可见其反程朱理学的内涵。平心而言,在易代之际,对情欲的鼓吹与肯定往往会远逾其他时期,就晚明而言,除了易代因素之外,思想上阳明心学嬗变的浪涛对禁锢情欲堤岸的冲击则是其独有的优势。
总之,在程朱理学和阳明本人的情感阐论中,更大程度上无疑落于伦理道德情感的范囿,即使阳明心学使人的个体自由得到解放,但是在道德领域,在阳明心学初期,这种道德上的自由还远未实现泰州道观寺庙寺院。可以说,不仅程朱理学的道德自由时时受到仁义规范及理性的制约,而且至王阳明,这种理性的制约依然存在,而这种对道德自由的束缚或许到晚明才得以真正解脱。可以说,时至晚明,道德自由开始摆脱外在的强力束缚而呈现为意志选择下的自觉、自愿行为,且这种意志的选择不以理性自觉为前提,而是以人的自然本真之反映为依据。
三、阳明后学重情说的文学投影及其理道向度
据上可知,阳明后学因背离阳明心学的“致”而过分强调“良知”,因而有跳脱理道的拘囿而有对个人情欲的强调,而这一转变也滋生了晚明文学重情说的蜂起,在此情形下,他们所主张的情在文学上投影后是否就必然和理道无关?恐怕还需辩证看待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一)重情说的文学投影及小品文的扬情抑理
P·史华罗曰:
与西方的理性至上不同,在中国的哲学著述中,很少考虑到个人的悲欢,新儒学的确立符合了对情感的最大控制泰州道观寺庙寺院。……在中国,难以驾驭的、自私的激情和得体的、合乎道德的情感只是同一个情感现象的两个方面。”[45]
诚然,中国哲学很少关注个人的情感诉求,而学人所论述的情感也大多需接受道德的节制泰州道观寺庙寺院。但是至王学左派,承祧阳明良知之学而变其本、加其厉,在“百姓日用即为道”的思想倾向下,他们对自然情欲的关注与诉求远逾前贤,故而他们主张的情感不复有温柔敦厚之意,而实际上入于“自私的激情”一途。是故,黄宗羲对温柔敦厚重新解读曰:
盖其疾恶思古,指事陈情,不异熏风之南来,履冰之中骨,怒则掣电流虹,哀则凄楚蕴结,激扬以抵和平,方可谓之温柔敦厚也泰州道观寺庙寺院。[46]
显然,黄宗羲反对将情感郁积心中而不敢吐露的传统温柔敦厚的意旨,认为喜怒哀乐应该随心而发,“激扬以抵和平”泰州道观寺庙寺院。显然,在阳明后学思想的影响下,传统的诗教观发生了变化,而这时的“性灵”主张大概展示了这一变化更为具体的内涵。范嘉晨等曰:
性灵文学思想在阳明心学为哲学基础的大环境下,与中国诗教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泰州道观寺庙寺院。可以简单概括为在心与物的关系中,虽没有否定物,但主观性灵在文学发生的过程中占据了主导,明显地表现出重视自我、重视主观心灵的倾向。……从而发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比如对情尤其是个体自然感情的重视。[47]
可见,“性灵”主张的实质已经将情感从国家、社会层面向自我层面回归,从而基本完成了由附庸于道德伦理的情向情感独立化和纯粹化的转向泰州道观寺庙寺院。而这一转向的突出表征便是在阳明后学“百姓日用即为道”的影响下,时人对日常生活以及其触发的情感给予了特别瞩目。例如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眉公语》条曰:“今日眉公(案:即陈继儒)见访,会将嫁女。孟氏言次及之,眉公叹曰:“大地一梨园也,伶人演戏先离后合。人生不然,父母妻子乃至骨肉,齿发刚合即离,真可发一笑耳。”斯语甚警,辄录之。眉公与予言,大都皆日用切实之务。然别后每觉意思翛远,寝食有味,真君子之言也。甲辰中秋前三日。”[48]这里张大复谓陈继儒之言“大都皆日用切实之务”,可谓一时风气的真实写照。当然,这种对日常生活的特别关注及相关情感的抒发在此期的散文创作上多有体现,尤其是在小品文写作中。
确然,这一时期如李贽等人确对自然情欲多有阐发,而这在文学主张上也有相当地表现泰州道观寺庙寺院。例如,袁宏道述说“去理”之创作过程曰:“一变而去辞,再变而去理,三变而吾为文之意忽尽,如水之极于澹而芭蕉之极于空,机境偶触,文忽生焉。”[49]而沈际飞论词之表情曰:
呜呼,文章殆莫备于是矣泰州道观寺庙寺院。非体备也,情至也。情生文,文生情,何文非情,而以参差不齐之句,写郁勃难状之情,则尤至也。……人之情,至男女乃极,未有不笃于男女之情,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间,反有钟吾情者。[50]
显然,这里的情已经脱离了儒家道德评价而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泰州道观寺庙寺院。而这一点在汤显祖关于理、情之辨的论述中彰显地更为明显,其论曰:
今昔异时,行于其时者三:理尔,势尔,情尔泰州道观寺庙寺院。以此乘天下之吉凶,决万物之成毁。作者以效其为,而言者以立其辨,皆是物也。事固有理至而势违,势合而情反,情在而理亡。故虽自古名世建立,常有精微要眇不可告人语者。[51]
以上汤显祖关于理、势、情的划分甚明,而其对“情在而理亡”的揭橥也可谓耸人耳目泰州道观寺庙寺院。可以说,“汤显祖标榜的这种性情之学,根基于人的自然本性,和性理之学是相对立、相背逆的。他有意高扬情的大旗,同程朱理学的性理相抗衡。《牡丹亭》所表现的就是这种情与理的冲突,即爱情作为人的自然本性和束缚人们身心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冲突。”[52]这样一来,与向前犹含有道德评价成分的情相比,此时的情在取得与理相对应的地位的同时,亦逾越了理(儒道)的界限而有了更为自由和独立的内涵。
而这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词等文学样式中均有所表露,而尤以小说、戏曲最为典型泰州道观寺庙寺院。鉴于诗、词、曲、小说等文体的“当行本色”本来就在于情感的抒发与腾跃,因此,这一时期的主情思想在这些文体上愈加显得突显并没有使人感到太大地诧异。这里要提及的是此期散文方面的转变,因为散文由于载道的固有惯性而不能骤然脱离“言志”的层面,因此在散文方面的脱离儒家道德评价的重情趣向或许更能突显时代氛围与学术思想“移风易俗”的卓越价值。可以说,“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在晚明时期颇为盛行。究其因,一则源于阳明心学影响下学人对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对自我的关注。二则因为国家已处江河日下之势,而人每多黄昏迟暮之感,于是亟需寻求精神的慰藉与怨世情感的发抒,小品文合乎时宜地发挥了这一作用。三是由于时人多任诞放达之徒,而“任诞发达之极,则疾当世,轻人间。疾世轻人之极,则连篇累牍,皆风云月露之状矣”[53]。在这样的情形下,因此有大量的小品文集及选集的产生。
而对于这一时期的小品文而言,“在情与理的关系方面,晚明激进派文人一般都扬情抑理泰州道观寺庙寺院。如,李贽、汤显祖、袁宏道都反对文中之理。”[54]不过时人言情之外,仍不乏言志载道的著述,这主要是因为“‘言志’和‘缘情’是站在创作主体的立场来说,‘缘政’和‘缘事’实从创作的外部要求而言。尽管‘志’更多倾向于书写符合群体要求的价值和立场,而‘情’倾向于表达个体自我的感受和意趣。……这种出自创作心境的差异而导致的文风不同,导致一个作家的创作分为两种基本的形态,使得作品有了两种不同的基调”[55],而这种创作心境的差异在大部主情的学人身上多有体现,因此,虽然此期的学人对言志载道作品颇有不满,但是这种传统作为文化积淀毕竟已深入人心,所以言志和言情的作品在他们的著述中往往并行而不悖。例如,主情去理甚笃的袁宏道,在大量创作闲适小品文的同时,也不乏积极干预社会现实的作品。尤其后期的袁宏道由狂禅入于净土,可见其由自适之情向重修持的转向,是以袁中郎曰:
逾年,先生之学复稍稍变,觉龙湖等所见,尚欠稳实泰州道观寺庙寺院。以为悟修犹两毂也,向者所见,偏重悟理,而尽废修持,遣弃伦物,偭背绳墨,纵放习气,亦是膏肓之病。夫智尊则法天,礼卑而象地,有足无眼,与有眼无足者等。遂一矫而主修,自律甚严,自检甚密,以淡守之,以静凝之。[56]
虽然这并非暗示着袁宏道由“缘情”向“言志”的迫近,但是庶几可以表明其思想上主情面向的弱化泰州道观寺庙寺院。此外,我们亦能发觉有的学人在论及情感时仍不免有或使之与理(道)并存,或使之归于理(儒道)的措辞,例如,郑元勋曰:
吾以为文不足供人爱玩,则六经之外俱可烧泰州道观寺庙寺院。六经者,桑麻菽粟之可衣可食也。文者,奇葩文翼之怡人耳目、悦人性情也。若使不期美好,则天地产衣食生民之物足矣。彼怡悦人者,则何益而并育之?以为人不得衣食不生,不得怡悦则生亦槁,故两者衡立而不偏绌。[57]
这里郑元勋在论及“文娱说”的同时,明言六经不可烧,可见其均衡二者的面向泰州道观寺庙寺院。但是尽管他们在现实创作上他们仍有载道的一面,在涉及情感时有依归理(道)的倾向,部分学人有主情观的弱化表现,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其思想上主情的实质。
(二)并非反动:世俗儒家伦理的转向
但是也需指出,此期的文学创作诸如言情之小品文中仍不乏载道言理的内容,从中可见其中道的一面,而且应该注意的是,尽管这一时期学人所言的情多超越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界限,但是看似背离儒道的表征改变不了此期士人骨子里的儒道热忱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即使时人有追求闲适之情而有轻载道的倾向,并且,考虑到这一时期学术界与思想界有会同三教的趋势,虽然此时的理(道)并非纯粹的儒道文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儒道在绝大多数人里仍然占据主流地位泰州道观寺庙寺院。即以当时盛行一时的“禅悦”之风来说,虽然家家谈佛说禅,但是似乎并不能改变其重儒学的事实。因为虽然“宋明时期的儒家……因受到当时佛道两家(尤其是佛家)在思想上的挑战与刺激,即所谓‘援佛入儒’的公案。……但是必须指出,深入思想内部来考察,则我们今天庶几可以断言,宋明儒的‘援佛入儒’只是借用佛家的一些想法与用语来扩大更新先秦儒家的睿识,而非‘阳儒阴释’”[58]。即以公安派的言情小品文而言,除了不能“以游堕事”(袁宏道《满井游记》)的思想发露之外,也未尝不是载道之外的另一种儒家思想的反映。质言之,他们虽然反对程朱理学要求文学“言志载道”的思想,但是未尝不符于儒家的天命之道与人性之道。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从陈来对王艮的评骘中得到解答。毋庸讳言,王艮由于对“尊身”的强调,从而使得阳明学说加入了功利的元素,而与传统的儒家伦理相悖,尽管如此,但是其思想中体现的思想并非对儒家伦理的反动,而庶几可归于“世俗儒家伦理”一途。陈来曰:
就一般的道德规范和道德修养来说,王艮并没有否定儒家伦理泰州道观寺庙寺院。……毫无疑问,王艮这些思想更接近于‘世俗儒家伦理’的特质,因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王艮的这些思想不应被视为理学的‘异端’,而是作为精英文化的理论价值体系向民间文化扩散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一种形态,其意义应当在‘世俗儒家伦理’的意义上得到肯定。[59]
依此而论,袁宏道等人小品文中体现出的“文娱”、重情思想何尝不是“世俗儒家伦理”的反映,其当然不是理学的“异端”,而同样是“作为精英文化的理论价值体系向民间文化扩散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一种形态”泰州道观寺庙寺院。此外,我们亦可从民国致力于小品文创作的学者那里得到启示。毋庸讳言,部分民国学人如周作人等人的小品文并不能简单粗暴地归属于吟花弄月、无病呻吟的作品,事实上他们的作品可谓是儒家“人生主义”传统的一种映射。对此,夏志清评论曰:
他(周作人)晚年大多数小品文都是报告读书心得,看样子是陶冶性情,过着闲适的生活泰州道观寺庙寺院。事实上,他是无休止向古人认同:理学传统圈外,竟还有不少思想活泼、头脑开明而关注民生疾苦的读书人。这些读书人,他认为延续了真正儒家的传统。……早在三十年代,周作人即不评论时政,尽心从事于儒家‘人生主义’新传统的建立。[60]
至于此期士人言语行为上背离理(儒道)的倾向似乎也不能断然否定与抹杀,因为其骨子里透显的仍然是理(儒道)文化信仰泰州道观寺庙寺院。而那些表面看起来的离经叛道倾向,在形塑他们反抗时代弊端的伟岸形象之时,亦未尝不是他们对原始理(儒道)做出的最真实地接近。以自谓狂痴的李贽来论,固然,其有诋毁圣贤儒道的叛逆之处,也有张扬纵欲的趋尚,然而其不讳过、不贰行、不矫揉造作、不沽名钓誉、不欺人、更不自欺,一任个性张扬、真情流露。如此之人,虽然每以离经叛道之言行举止示人,但是恐怕并不能断然认定其即儒道之罪人。虽然李贽身上存有矛盾的一面,其绝意仕进,而又专谈用世;其操若冰霜,而又深恶枯清、刻薄;其本屏绝声色,而又重视情欲。如此诸种,不一而足。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些矛盾,方才是其具“童心”而为“真人”的真实展露。至于其外显为离经叛道的狂谬表现,诚不宜轻易痛诋贬斥。质言之,其所叛者,形式上之儒道,程朱之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之道,而绝非纯粹的儒家本原之道。这样的狂在李贽看来,不过是“借助‘大言’自高位置和愤世嫉俗而已。换言之,‘狂’更多是在他人的眼中呈现,是‘观者见其狂’,‘观者’们越视‘狂’为‘猛虎毒蛇’,避之唯恐不及(‘相率而远去’),‘狂者’就越是感到自幸自喜,口出的狂言越发肆无忌惮(‘唯恐其言之不狂’)”,而就其本质而言,其实狂“并不是李贽所追求的目标,只不过是他生命的一种状态。相反他追求的是‘圣’,不依循传统解释的与伪绝缘而又生气昂然的‘圣’。因此他不认为‘圣’与‘狂’是不能两立的品格。”[61]
综上可知,在阳明的心学体系中,固然有对自然情欲的肯定,但是其主张的情毕竟还隶属于道德情感的范囿而未完全独立,这一点在去阳明未远的唐宋派那里依然如此泰州道观寺庙寺院。而至阳明后学王畿、王艮等人处,由于对阳明心学思想的鼎革,使得阳明心学肯定自然情欲的一面得以愈加彰显,从而造就了时人对“实实在在的‘我’的血肉、情欲和自然需要”[62]的重视,进而使得明代士人的内在情欲得以最大程度的解放而无需压抑。这样一来,在文学领域内,主情倾向成为大势所趋,众多文学样式如戏曲、小说、诗、词等都宣露了对“情感说”的强调,而尤为典型的是,历来以载道言志为传统的散文领域也出现了向重情转变的可喜变化。
向上滑动查看注释
[1]郭英德、谢思炜等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15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2]苏伯衡《空同子瞽说二十八首》,《苏平仲文集》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28册,第842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3]郭英德、谢思炜等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63464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4]李梦阳《缶音序》,《空同集》卷五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62册,第477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5]康海《美陂先生集序》,《对山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1266册,第342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6]章培恒《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安徽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7]徐祯卿《谈艺录》,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68册,第778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8]王运熙、杨明著《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泰州道观寺庙寺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103 查找
[9]郭英德、谢思炜等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绪论》,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4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10]牛月明《中国文论构建研究——因情立体、以象兴境》,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11]刘松来著《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92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12]詹福瑞著《中古文学理论范畴》,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13]李梦阳《张生诗序》,《空同集》卷五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62册,第470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14]以上参引李梦阳《林公诗序》,《空同集》卷五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62册,第469470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15]康海《送白贞夫序》,《对山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1266册,第347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16]王世贞《送李伯承之新喻令序·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五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80册,第10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17]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157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18]黄毅《唐宋派文论的重新评价》,《中西学术》,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19]王阳明撰,邓艾民注《传习录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40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20]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47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21]陈来《王阳明哲学的理解与阐释》,哲学研究,1991年第1期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22]宇文所安著、田晓菲译《他山的石头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23]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辑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24]王阳明《与许台仲书》,《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2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25]郭美华《与朱熹王阳明对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26]李攀龙《送王元美序》,《沧溟先生集》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78册,第369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27]黄绾《明道编》卷第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28]陈谷嘉《明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29]彭国翔《阳明后学工夫论的演变与形态》,《浙江学刊》2005年第1期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30]陆树声《清暑笔记》,《陆学士杂著十种》,吴门马凌云刻本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31]王禹卿编著《王阳明之生平及其学说》,正中书局1946年版,第80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32]黄宗羲著、沈芝盈校点《泰州学案一》,《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03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33]黄进兴著、郝素玲等译《李绂与清代陆王学派》,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95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34]章培恒《试论凌濛初的“两拍”》,《晚明文学思潮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35]冯梦龙《王阳明出身靖乱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36]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47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37]袁黄《情理论》,《明文授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00册,第391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38]欧文《追忆——中国古典文学的往事再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64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39]沟口雄三著、郑静译《中国的公与私》,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12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40]沟口雄三著、郑静译《中国的公与私》,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7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41]杨国荣《善的历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42]章太炎《菿汉微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43]袁宏道撰、钱伯城笺校《董思白》,《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89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44]黄绾《明道编》卷第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45]P·史华罗著、庄国土、丁隽译《明清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心境词语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9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46]黄宗羲《万贞一诗序·南雷诗文集(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495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47]范嘉晨等《晚明公安派性灵文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48]张大复《梅花草堂集》,《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十二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213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49]袁宏道《行素园存稿引》,《袁宏道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5701571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50]沈际飞《诗馀四集序》,《古今词统》,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728册,第447448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51]汤显祖著、徐朔方笺校《沈氏弋说序》,《汤显祖诗文集》卷五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1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52]郭英德《痴情与幻梦——明清文学随想录》,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83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53]刘永济《文学论、默识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4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54]周群《徐渭文艺观的另一面相:中道》,江海学刊,2015年第4期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55]曹胜高《中国文学的代际》,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20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56]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柯雪斋集》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58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57]郑元勋《文娱初集序》,明崇祯三年刻本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58]郑宗羲《明清儒学转型探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59]陈来《宋明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60]夏志清《人的文学·感时忧国》,广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80281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61]以上参引刘梦溪《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6062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62]李泽厚《华夏美学·美学四讲》,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10211页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全 文 完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原文发表于《斯文》第六辑
作者介绍
常威
周口师范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学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本文章由京师文会出品泰州道观寺庙寺院,转载需同意
欢迎投稿泰州道观寺庙寺院, 稿件请发至
jingshiwenhui@163.com
长·按·关·注
▲向上滑动
WEN
HUI
jingshiwenhui
顾问
郭英德 李小龙
主编
诸雨辰
图文编辑
曾子芮 林丹丹
冯浩然 谢宜君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
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心
中华文化研究与传播学科交叉平台
免费测八字 今年运势 请加师父微信

免费看八字运势 请加师父微信: fuyuntang8
寻找符咒,灵符,符咒网,道教符咒网,灵符网站,灵符网官网,购买符咒请灵符,这里有各种手绘开光符咒:财运符,财运符咒,财运亨通符咒,五路财神符咒,太岁符咒,化太岁符咒,回心转意符咒,护身符咒,文昌符咒,学业灵符符,开运符咒,转运灵符,桃花符,月老姻缘符咒,偏财符,五鬼运财符咒,化小人符咒,事业符咒,升官符咒,去病符咒,去疾符咒,健康符咒,平安符咒,夫妻和合符,情感和合符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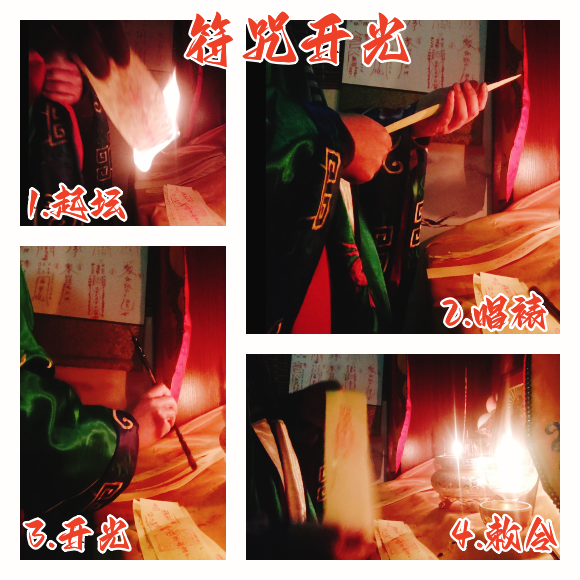
咨询道教符咒 咨询师父微信: fuyuntang8
符咒类型如下:
01.财运符-增财运补财库开运 02.太岁符-化解不利顺利度过 03. 回心符-挽回感情增缘复合 04. 护身符-辟邪镇宅转运护身 05. 学业符 -魁星点斗文昌帝君 06. 开运符-开运转运驱除霉运 07. 桃花符-桃花早到月老姻缘 08. 偏财符-五鬼运财偏财运势 09 .小人符-化解小人是非口舌 10 .事业符-事业有成无往不利 11. 去疾符-药王化疾祛病消愈 12. 健康符-身心健康得偿所愿 13. 平安符-诸事顺利健康平安 14 .和合符-夫妻情感姻缘和合 15.定制符-心有所想 专属定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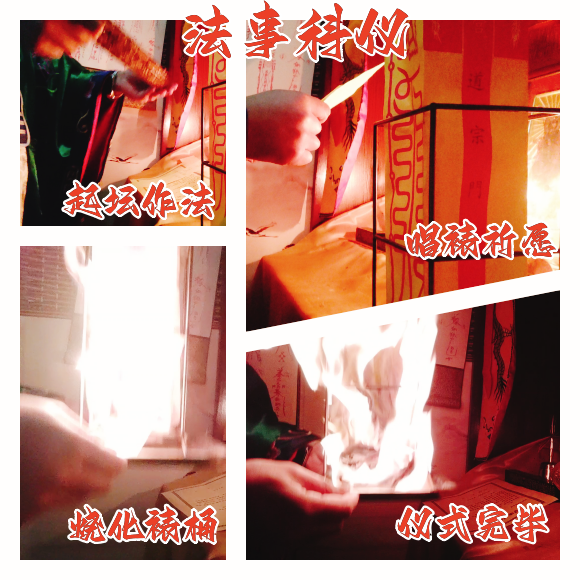
咨询道教法事 咨询师父微信:fuyuntang8
01.化解太岁法事——解太岁、谢太岁 02.升官晋职法事 ——官运亨通提升政绩 03.文昌考试法事—— 开窍聪慧考试顺利 04.偿还阴债法事—— 生债阴宅逢凶化吉 05.开财门补财库—— 增加财运助旺事业 06.助种生基法事—— 病魔缠身增寿增运 07.催子受孕法事—— 生子布阵子女满堂 08.开运转运法事—— 改运天命一帆风顺 09.催财发财法事—— 偏财运势正财持久 10.化解童子法事—— 姻缘顺利仙灵护佑 11.化解小人法事—— 化解小人防人陷害 12.小儿平安法事—— 驱邪回魂活泼健康 13.超度亡灵法事—— 祭奠亲人早登极乐 14.超度宠物法事—— 人类朋友转生脱苦 15.超度婴灵法事—— 打胎坠胎消灾除难 16.祈福许愿法事—— 许愿还愿祈求祈福
本文链接:https://fuzhouwang.org/index.php/post/7088.html
转载声明:本站文章中有转载或采集其他网站内容, 如有转载的文章涉及到您的权益及版权,还麻烦及时联系我们,我们将及时删除,谢谢配合。
